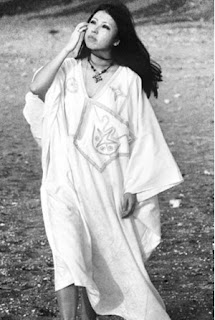 三毛,似乎就是一个没有人不认识的女作家。近来在办公室里,总听到有关她的故事,而我对她的印象却只有“耳闻”。李老师问吴老师,“知道三毛是个怎样的女生?”(此时我走进办公室)李老师看着我,“就是像她这样!”坦言,那个时候的我是一头雾水的,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三毛。
三毛,似乎就是一个没有人不认识的女作家。近来在办公室里,总听到有关她的故事,而我对她的印象却只有“耳闻”。李老师问吴老师,“知道三毛是个怎样的女生?”(此时我走进办公室)李老师看着我,“就是像她这样!”坦言,那个时候的我是一头雾水的,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三毛。
今年年初在食堂买饭的当儿,身边的陈老师问我,“你又要到哪儿浪迹江湖”?(去年12月刚从尼泊尔徒步归来)我当下,竟非常理性地说“现在要上班”。陈老师沉默了会儿,最后说“你认识三毛吗?”我笑笑回答着“认识”。而他却道出“你和她很像”!又如此之巧合的是,我这几个月来,不断地在读三毛的传记和作品。
 三毛,原名陈懋平,再看她的生平,我有着无数的惊叹。小时,一向数学极差的她,在某次测验拿了满分。可这不但没有得到鼓励的话语,反遭了对她一辈子难忘的惩罚。老师不信任她,还在她的眼睛上画了两个大圈,这是何等的讽刺,又何等地耻辱!身为一位老师,我们得警戒自己。我们也得适当去聆听孩子的话语。偶尔,我们或许有太多的先入为主,或许忘记了孩子的苦衷;又有太多个人的主观,或许又忘记了孩子还是那么小;我们就自以为是地发起脾气,更自以为我们是替孩子着想。但,真的是为孩子着想吗?还是我们只是希望,孩子做到我们所如愿的?这不免又让我想起高二的课文中所提及的“两代人的矛盾”。
三毛,原名陈懋平,再看她的生平,我有着无数的惊叹。小时,一向数学极差的她,在某次测验拿了满分。可这不但没有得到鼓励的话语,反遭了对她一辈子难忘的惩罚。老师不信任她,还在她的眼睛上画了两个大圈,这是何等的讽刺,又何等地耻辱!身为一位老师,我们得警戒自己。我们也得适当去聆听孩子的话语。偶尔,我们或许有太多的先入为主,或许忘记了孩子的苦衷;又有太多个人的主观,或许又忘记了孩子还是那么小;我们就自以为是地发起脾气,更自以为我们是替孩子着想。但,真的是为孩子着想吗?还是我们只是希望,孩子做到我们所如愿的?这不免又让我想起高二的课文中所提及的“两代人的矛盾”。  在友人的陪伴下,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。看了三毛的生平,那简直就是传奇的生平。三段感情的坎坷,不断地流浪的她,我们其实在羡慕她什么?在这之前,我听过多少人说,她羡慕三毛可以到处流浪,或看了三毛,希望自己也可以随她一样流浪去。但今天,她的流浪是承载着多少的代价?因为荷西的离开,她“有幸”开始流浪,可她的心灵有太多的伤口。最终到底是死于她的病,还是自杀,我们真的有办法断定吗?
在友人的陪伴下,我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。看了三毛的生平,那简直就是传奇的生平。三段感情的坎坷,不断地流浪的她,我们其实在羡慕她什么?在这之前,我听过多少人说,她羡慕三毛可以到处流浪,或看了三毛,希望自己也可以随她一样流浪去。但今天,她的流浪是承载着多少的代价?因为荷西的离开,她“有幸”开始流浪,可她的心灵有太多的伤口。最终到底是死于她的病,还是自杀,我们真的有办法断定吗?  从网络资料显示,大家都爱用《不死鸟》来作为一个例子,而友人也建议一读。开篇就是回忆一年多前她和荷西的对话。打的引子既是那么地沉重“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寿命,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”?荷西问她的看法。但三毛并无正面回答,只是说“傻子,我不会死的,因为还得给你做饺子呢!”文章就是围绕这个生命的课题而展开,但在她思索后的答案,却让我觉得我们正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了吗?她说: “我要守住我的家,护住我的丈夫,一个有责任的人,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。”说的极好的。但,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控制死亡。我们能做的,就是好好珍惜,好好把握当下。这些话,没有人不会说,但我们正视我们自己活着的意义吗?确实珍惜了吗?把握了吗?我不像三毛想要预知自己的死期,因为我同她一样,是拒绝死亡。我如他人的贪婪,想要的更多,想要为自己的生命争取更多的东西。但我不能控制时间。我只能尽可能在我的生命里去寻找我想要的东西,我想要的梦想,甚至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反观,对于此时的三毛而言,家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。
从网络资料显示,大家都爱用《不死鸟》来作为一个例子,而友人也建议一读。开篇就是回忆一年多前她和荷西的对话。打的引子既是那么地沉重“如果你只有三个月的寿命,你将会去做些什么事”?荷西问她的看法。但三毛并无正面回答,只是说“傻子,我不会死的,因为还得给你做饺子呢!”文章就是围绕这个生命的课题而展开,但在她思索后的答案,却让我觉得我们正视我们自己的生命了吗?她说: “我要守住我的家,护住我的丈夫,一个有责任的人,是没有死亡的权利的。”说的极好的。但,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控制死亡。我们能做的,就是好好珍惜,好好把握当下。这些话,没有人不会说,但我们正视我们自己活着的意义吗?确实珍惜了吗?把握了吗?我不像三毛想要预知自己的死期,因为我同她一样,是拒绝死亡。我如他人的贪婪,想要的更多,想要为自己的生命争取更多的东西。但我不能控制时间。我只能尽可能在我的生命里去寻找我想要的东西,我想要的梦想,甚至是我想要的生活。反观,对于此时的三毛而言,家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。
在荷西死后不久,她曾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可,在挽救回来后她写了此篇(《不死鸟》),她表示“在这世上有三个与我个人死亡牢牢相连的生命,那便是父亲、母亲、还有荷西,如果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在世上还活着一日,我便不可以死,连神也不能将我拿去,因为我不肯,而神也明白”。在《明日又天涯》里,那看不到永恒的每一天,然而“一屋的寂静里,我依旧吹着那首最爱的歌曲——《甜蜜的家庭》”。哪怕三毛不只一次地认为,死亡是“幸福的归宿”,但为了父母,她坚持下来。虽说至此的论据,大家会将三毛的死因定在非自杀,但这会不会太断章取义了呢?毕竟后期的她,患上了无人可控制的忧郁症。这叫人悲哀,也叫人伤痛。
她爱荷西,爱得不可自拔。哪怕只有短短的6年。她的一段话,尤其让我感触。“我总是在想荷西,总是又在心理自言自语:‘感谢上天,今日活着的是我,痛着的也是我,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一分又一分钟的长夜,那我是万万不可的,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......’”后又补充道,“要荷西半途折翼,强迫他失去相依为命的爱妻,即使他日后活了下去,在他的心灵上会有怎么样的伤痕、会有什么样的烙印?”。我脑子里想起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。虽然不同时代,不同个性的两个人,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,因为爱,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离去给对方带来种种的痛。想过吗?我们会怎么去处理仅剩的三个月?如果......如果......
我不曾想过,更不曾认真地思考。但对于爱出走的我,我希望和家人一起出走,和他们共创最后的回忆。这会不会很自私?我不清楚。我听说,因为要让自己死的安心,结果无意识给活着的人带来众多的痛苦。这个回忆,到底是给谁的?给自己的?给活着的人的?我仍旧不清楚。作为他人的朋友,他人的家人,我希望我能留给他们什么,哪怕只是一纸的荒唐言、哪怕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礼。如三毛所言:“先走的是比较幸福的,留下来的,也并不是强者”。
三毛毕竟是留下的那个,虽为了家人而坚强地继续存活,但在《明日又天涯》里,我看到她依旧思念、依旧盼望着他。对她而言:“明日,是一个不能躲避的东西,我没有退路”/“Echo的明日不是好玩的。”。确实,不管对世间上的任何人来说,都是如此。可,我们的心态不在于“躲避”而是为我们自己的“拖延”寻找另一个出口。甚至,有着期待、有着规划。或许真的如三毛那般的不好玩,但我们还有一颗继续走下去的心。换个角度,三毛认为:“昨日的风情,只会增加自己今日的不安全”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她只剩下一个人。虽然“青春结伴”,她“已有过,是感恩,是满足,没有遗憾”。她的转折,似乎让你看到希望,但实际并非如此。只因为,三毛认同,有谁在这个世界上,“不是孤独地生,不是孤独地死”?是啊,有谁不是,又有谁是例外,除了历史上所谓的殉葬?其实又有谁知道,我们到了地府真的能够相见呢?







No comments:
Post a Comment